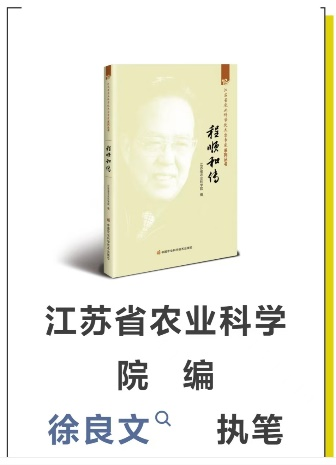
屠生楷
提起我国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相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他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而提起我国的小麦育种专家程顺和院士,知道的却不多。其实,他同袁隆平院士一样,是我国育种界的十大功勋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被誉为“南方麦王”。
有人说他为种子而生,也有人说他就是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就有一粒种子的故事,一粒种子就有一粒种子的成长历程。倘若您想探寻这位育种界翘楚的人生轨迹,那么就请和我一起翻开著名作家徐良文先生历时五年倾情撰写的《程顺和传》吧。
程顺和从襁褓中开始就跟着家人躲鬼子跑反,饱尝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父亲死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弟拉扯大。日子过得极为清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桌上摆满了白花花的米饭和馒头……
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她常常给儿子讲故事:孟母三迁、萤囊夜读、凿壁偷光……教导儿子要有志气,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些教导如雨露一样滋润着程顺和的心田,培育着他内心向善的种子。
“在艰难的世道中,在贫瘠的土地上,程顺和生命的种子在顽强地发芽、生长。”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1958年9月程顺和考入南京农学院,主修小麦选种专业。开学仅几个星期便下到农村劳动实践,这段经历让程顺和亲身感受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的不易。
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稀缺。程顺和家乡溧阳旁边的安徽郎溪,树叶都让人撸光吃了,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一头跌下去再没爬起来。这让程顺和充分认识到粮食的可贵,对农作物育种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他感到了一种使命和责任。他梦见自己培育出的良种放了卫星,打出了1万多斤。
毕业后程顺和被分配到泰兴县稻麦良种繁育场。为了拿出完善的试验计划,他白天去田头测量,计算开墒、挖沟、间距、行宽;晚上仍在床上思考他的育种方案,一夜起身三四次。他在地里扛着鞭子赶牛扶犁、开拖拉机……
有人说:“程技术员,你在技术上把把关就行了,这种翻地挖沟的粗活我们来干。”他这样回答:“种子只有投入大地,才能开花结穗。我要是连种地这种活都不能干,还怎么育出好品种?”
终于,他培育出的泰农一号面世,亩产达到了800斤。
![]()

照片说明:徐良文(左) 程顺和(右)
1968年“文革”期间,程顺和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在干校,他把“泰农一号”和扬州地区农科所的“扬麦1号”分别种在试验田里,观察二者的生长区别。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小麦育种梦。但干校不是实验场所,不允许个人搞什么研究,大呼隆收割,程顺和无可奈何,就这样被迫中断了小麦育种6年。
然而种子从不因为被埋没而放弃向上的追求,他在泥土中等待,在黑暗中寻找光明。6年后,他终于被调去了扬州地区农科所,重启小麦育种。
育成一个新品种非常不易,一个单株种一行,叫株行,好的株行把它收起来,种成小区,再放大,年复一年,从好的里面选好的,从低代到高代,层层选拔,最后进行区域试验,区域试验要做两三年,反复检验、淘汰。区域试验通过后便是生产试验,生产试验两年后才可以进行审定,审定通过了,才算出一个新品种。材料的培养和选择要经过十数年,区试和审定又要好几年,绝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里分配给程顺和一间工作室,作为他午间休息的宿舍,但中午时分正是观察小麦生长的最佳时段,宿舍里基本看不到程顺和,大中午他顶着太阳蹲守在麦田里。别人下班回家了他留在宿舍里记笔记、看资料。到了夜晚,那间宿舍里又亮起了灯光,这时程顺和就在灯下整理分析白天的观察心得和学习新理论。
为了把目标性状诱变出来,他为农科所申请来了钴源。妻子担心地说,“如有疏漏,钴源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你不怕?”他笑笑:“怕这怕那,还搞什么科学实验?”年三十下了雪,他为了去雪地实地察看麦苗的变化,竟忘了家中煮着饺子……
选择小麦育种,就是选择寂寞,选择坚守,选择执着。程顺和的一生就是这样,忍受孤独的煎熬,忍受失败的痛苦,无数个夜晚,上万次的试验,无尽的思考,面对土地,怀揣对一种新生命的期待,看它发芽、分蘖、开花、扬穗、成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眼中枯燥无味的生活,在他心中却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
终于,他主持育成的扬麦 5号、扬麦158分获1991年、199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我国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扬麦158初步解决了世界小麦育种中广适高产与抗赤霉病、白粉病的难题。
成功后的鲜花和荣耀似乎与他无关,他仍然沉湎于实验室、试验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他的心中只有小麦、小麦……
市委领导欣赏他,想把他调到科委去。科委是领导机关,待遇比农科所好,朋友们都劝他去,程顺和不为所动,他笑说自己不适合官场,要留在农科所钻研他的良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奖励程顺和30万元奖金,他将其中的1万元捐给希望工程,10万元设立科研奖励基金,其余的全部用于感谢常年奉献在农科所小麦育种的课题组人员以及长期支持小麦研究的人员,自己一分钱也没留。
有人问程顺和荣获国家大奖后有什么感想?程顺和面色平静,语调平缓地说:“获奖当然高兴,说明你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承认。但获奖不是目的,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才是目的,我们搞育种的,奖章是挂在麦田里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会上,麦农把包好的一束麦穗像献花一样献给了程顺和。种子的档案,只在泥土里贮存;麦子的重量,只在百姓的麦秸上记录。
程顺和培养后辈人才不遗余力,他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手下的弟子如今都已挑了大梁。为了留住人才,他亲自为他们介绍对象。他同弟子们开玩笑:“你们找对象、谈恋爱,也要像良种审定那样,要看综合性状。”
程顺和积劳成疾,得了肺纤维化病。朋友陆维忠说:“这病很严重的,千万不能大意!都这把年纪了,你就先把赤霉病的事放一放,去医院好好查查自己的病要紧!”程顺和点头说道:“医生也这么说,我记住了,回头就去医院查查。但你也别忘了咱们说好的小麦赤霉病的事!”
回到扬州,他把朋友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什么肺纤维化,他根本不当回事。他认为,倘若生命真的进入倒计时,那更不能停歇前行的脚步,要加快科研的进度,与死神争夺时间。他的生命能量在不断透支,灌输到那无数的麦穗和无尽的麦田之中……
陈顺和是育种界的杰出代表。在他前面还有像金善宝、吴兆苏、陈道元等一大批为小麦育种事业奉献了一生的科技工作者,作者在书中也不吝笔墨去讴歌他们,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态度:这些曾为我国的育种事业默默做出过贡献的人都不应该被忽略、被委屈、被忘记!
作者徐良文老师用了五年的时间对程顺和院士本人及其助手、同事、亲属、学生、知情人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以他如椽的巨笔书写了一个大科学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形象丰满、立体、生动、感人。书中没有火山爆发似的煽情语言,也没有巨浪冲击闸门似的情感宣泄,他的文字如涓涓细流,平实而又清丽,有信度又有力度。那烟波浩渺的太湖,秋雾弥漫的瓜州渡,荷风阵阵的瘦西湖,是作者为我们精心营造出来的真实而又唯美的意境。
作者多处用到古诗词:李太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陆游的《时雨》,姜白石的《扬州慢》,还有有关瓜洲的几首唐诗等等。这些古诗词用得恰到好处,既渲染了气氛,又极具艺术感染力。特别是结尾处摘用《诗经•大雅•生民》的那一段更是画龙点睛,深化主旨,给读者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